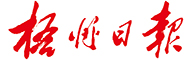“隽隽,出去吃朝啦,你要吃什么?”
“不知道。”
“不能说不知道,想吃什么就直说。”
“说了你又不去。”
休息日的早晨,外出吃朝前几乎都要跟女儿做一次如此这般的对话,每次拉扯的结局,都是我先投降:“好啦,知道你要吃螺蛳粉。这样,妈妈吃石磨米粉很快,你先陪我吃,然后我再陪你吃。”
这就是我跟女儿在吃朝这件事上不可调和的矛盾。
在岑溪,一日三餐的叫法,分别为“吃朝”“吃晏”“吃夜”。岑溪的传统早餐,大而化之地说,是一碗粉,一碗粥。
粉,在市场卖的,专指石磨米粉,石磨磨出来的丝滑米浆,薄薄地在金属托盘中蒸出一张张透明洁白的粉片,折叠后用菜刀切条,夹到碗里浇上料汁拌匀,软糯爽滑,鲜香盈口,是很多老岑溪人的心头好。因吃石磨米粉,有卤的猪隔山肉、猪耳朵、炸的猪肠、叉烧、烧鸭、白斩狗肉等佐餐伴食,是以早晨时间充裕的人们,会让店家切上一碟卤味烧肉或斩来一碟狗肉,叫上几碗石磨米粉、二三两本地米酒,米粉搅匀汤汁,卤味熟肉蘸香口料水,二三对酌吃起来,不比广东喝早茶的乐趣少。
上周末,我在一直喜欢的石磨米粉店吃朝,看到隔壁桌的老爷子碰到熟人,两人一番寒暄,决定酌几杯,于是重新让店家添了肉酒,吃着喝着,就聊开了。坐在简陋的石磨米粉店吃粉,吵是吵点,胜在市声入耳,充满人间烟火味,听、谈、观、食,四件事依托一碗粉,自有意趣在其中。
如若在家吃粉,大多就是煮或炒三堡米粉了。三堡米粉是统称,其实就是石磨米粉的晒干切丝版本,岑溪多个镇均有出产,但以三堡镇做得最好吃,因而得名。三堡米粉以其柔韧如丝、米香浓郁吸引人,放点鸡蛋或肉片煮成汤,米粉放下去,肉蛋鲜味大都吸入粉内,筷子夹起,一口爽滑,配菜的鲜味悉在其中。若是炒着吃,虽然少了满口鲜汤加米香的清爽,却又成为肉香、粉香加镬气的组合感受,一筷子接一筷子夹起、吃下,欲罢不能。炒米粉是个技术活,火候掌握不好,或是加水加汤不及时,就会炒成黏糊一团,跟高手炒得根根粉丝分明、肉味调料均匀到位不可同日而语。
而粥,是岑溪人在家吃早餐的常态。煮一锅白粥,炒一碟青菜,这是家庭日常早餐的标配。勤快点的,在白粥里加些粟粉,煮成红汤白米的粟粥,比白粥好看、滑口又健脾胃,对于追求食补的岑溪人来说,选它,肯定不会错。我母亲肠胃不好,粟粥是每日必食,如若反胃作呕,用纯粹的粟粉煮成粉浆,吃一碗下肚,就消停不少。是以岑溪人爱粟,米店常年有粟粉出售。其他还有祛湿粥、杂粮粥,都是食补食疗之粥,每隔一段时间,岑溪人都会煮一锅粥来吃。
外出吃粥,以上的粥都买得到,但是买着吃的粥,还是以猪杂粥为主。小城里吃的猪肉,都是一大早劏好的猪送到市上卖,赶早买到的猪杂最是新鲜,马上洗净切片,放油盐料酒腌好,粥滚米开就放入粥里滚熟,撒入葱花,加些胡椒粉,大家常说“一碗猪杂粥吃热一个早晨”。岑溪人有过午不吃猪杂的习惯,就是因其吃而必鲜的饮食习惯。买到的猪肝中午吃不完,晚上再做菜时,母亲肯定在灶旁盯着我,必须煎炒着吃。母亲已不在多年了,如果老人家还在,我会告诉她,现在岑溪又兴起吃油茶粥,成为外来粥品中最得人心的一种,不知她老人家是否爱吃。
可惜以上提到的岑溪传统吃朝品种,女儿都不买账。一说起吃朝,言必称螺蛳粉,桂林米粉已是退而求其次,南宁老友粉又次之。一家人出去吃朝有矛盾,在家吃朝更是难调众口,唯有备一瓶老干妈,无论煮粉炒粉,挖一勺放下去,总算是稍合年轻人口味了。
但是看到每逢节假日,石磨米粉和猪杂粥的店铺旁边停满不是本地车牌的小车,从车上下来的又都是讲岑溪本地话的年轻人走进店里大声叫:“老板娘,两盅隔山粉,不要葱,要少点辣椒!”或是:“三份猪杂粥,炒碟壅菜、炒碟米粉!”这些年轻人接受了家乡的吃朝口味,那是他们已经深深感受到一个叫做“乡愁”的空洞要用石磨米粉、三堡米粉、粟粥、猪杂粥来填补了,那么,传统的岑溪吃朝口味,就都是他们在回到岑溪时的吃朝选择了。